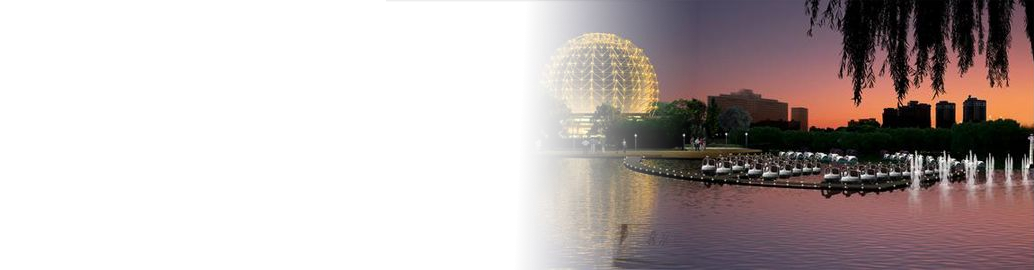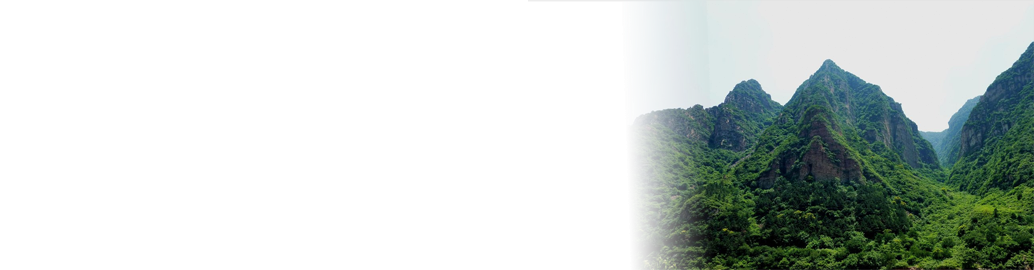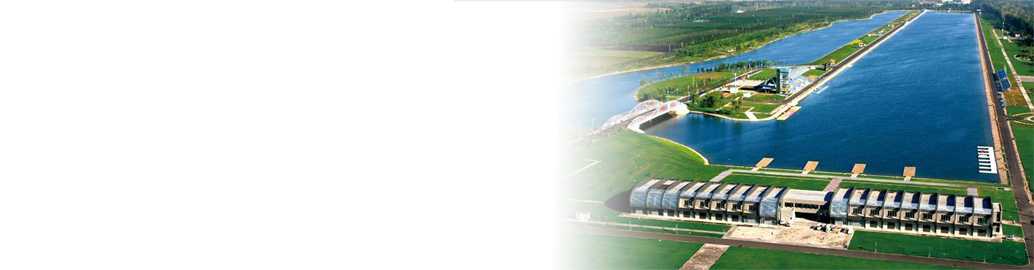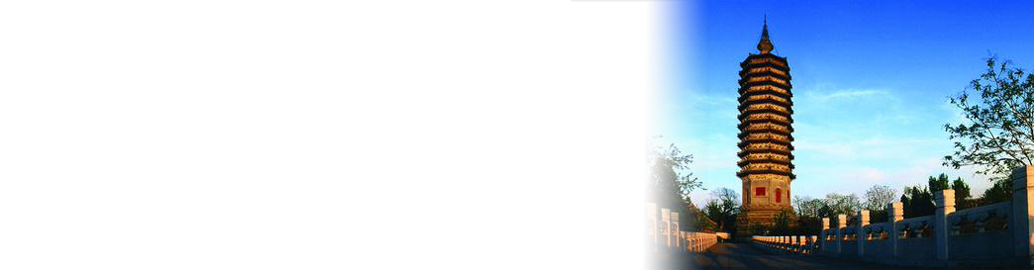“每天在办公室,都干些什么?”“还没走,忙啥呢?”“您好,我来拿信,请问哪位是刘辉?”……这是一位部队的老兵、法院的新兵——刘辉2015年10月转业到三中院以来常常听到的问话,而这些问话的答案就在我下面要讲的故事里。
刘辉,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监察室副调研员,1973年生于河北沧州。1991年入伍,2015年从部队转业到三中院工作,我们称为“辉哥”。
辉哥的家乡沧州,俗称“武术之乡”,出武夫,是招兵人青睐的地方。当兵,那时候也是一条好出路,“因为能吃饱饭呀”,辉哥说,“白花花的馒头,管饱。可不是想去就能选得上的”。辉哥年轻时练过武,父亲也当过兵,也算是行武出身,就在1990年幸运地跟着招兵人走了。
从当“大头兵”起,辉哥在部队一干就是25年。期间,他上了军校拿到本科学位,提了干部开始自己带兵,奋斗多年终成团职领导,当然也从一名新兵变成了老兵。20多年间,他从河北沧州到山西太原,从山西太原到北京通州,从北京通州到北京房山,前前后后搬家7次,辗转多年终于在北京清河扎下“根”。
在清河部队大院选房那年,一家人刚刚回到河北老家准备过年。来电话那天,从沧州回北京的最后一班车都没有了,辉哥只能全权委托部队同志第二天代自己去选。第二天天还没亮,辉哥就搭车一路往北京赶,车还堵在进京收费站时,楼层门号选定的消息传来,辉哥心头的一块石头“咚”地一声落了地。消息传回老家,只听见电话那头,静候着的媳妇和小子激动地“啊”的一声。辉哥说:那时候只想到一句话,二十多年,终于不用再搬家了……
2015年,在军队改革的大背景下,辉哥选择脱下军装,转业到地方做一名普通干部。在聊天时我了解到,辉哥转业的原因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小子。辉哥的小子当时14岁,已经上初三了,正是学业紧张的时候,同时也正处在青春叛逆期。从军20多年里,辉哥把自己的时间都交给了部队,孩子基本由媳妇照顾长大,母亲的慈爱、父爱的缺失让孩子更容易叛逆。多半儿是因为对孩子的亏欠、对媳妇的愧疚,辉哥决定转业了。10月9号,辉哥到三中院监察室报到,开始负责纪检监察信访投诉举报处理工作,以“从头再来”的姿态开始了一名“新兵”的征程。
作为“新兵”,辉哥仍然保持着“老兵”的样子,因此看起来与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干部有明显区别:由于开始多半年没有制服,他自己买了一身黑色的西装。虽然是“冒充”的制服但他却非常珍惜,总是打理的整齐笔挺,还借了一个法徽郑重地戴上。此外,他对部队以前发的衣服也非常珍惜,天冷了要套上部队发的印着国旗的毛背心,长年穿着部队的厚底“三接头”皮鞋和军用棉袜。平时,他走起路来总是昂首挺胸的,军人气质十足。交待起事情来,总是大眼一瞪、双眉一锁,习惯性顿一下再接着往下讲。说话的语气总让人感觉直杠杠的,一股浓浓的尚武老兵风味就出来了。工作之余的辉哥也不总是这么“严肃”。其实他喜欢热闹,爱开个玩笑,无论在电梯间,餐厅里,还是班车上,他会主动上前,跟“老哥”、“老妹儿”们打声招呼,和同楼层的一对“铁姐妹儿”逗句乐,跟同样带过兵的转业老兵们拉个家常,探讨骑车回家的最佳路线和教育孩子的奇思妙想,也是笑声不断。
辉哥刚开始接手信访处理工作时,领导们都有些担心。这种担心并不多余,因为他虽然上军校时学过法律,但多少年没用过。甚至连什么是一审、二审、再审,什么情形下法官需要“回避”等等最基础的法律专业问题都不太明白了,纪检监察业务更是属于“连猪跑都没看过”的状态。因此对他来说,一切都得从零学起。就像刚刚剃头入伍的新兵从练习踢正步开始一样。
为此,自报到之日开始,辉哥就找了一本诉讼法的书,对照信访件反映的内容翻来翻去、念念叨叨。遇到实在弄不懂或看不明白的就问。这时候,我和小田,两位被他称为“小老妹儿”的新兵,就升格为“师傅”。虽然是请教,但他不会简单地说“是”,而是常与我们辩一辩,直到最后弄明白或找到具体的规定在哪条哪款。不光自己在办公室里看,中午吃饭、上下班坐班车都是学习的好机会。辉哥爱和大家伙儿拼桌,主动说说部队的事儿,听大伙儿聊聊开庭的程序,慢慢就熟络了。再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,就在聊天的空档里顺便听听法官们的意见,对应着信件里反映的情况,慢慢就能对不同的信访件分类理解了。
学习和请教,不仅是为了对信访分类处理,因为辉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回复当事人。出于对当事人负责和化解矛盾考虑,三中院监察室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——“初访必复”,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刚开始,辉哥也会控制不住自己,刚跟当事人说几句脸就红了、声也大了、气也粗了,就差吵起来了。慢慢地,随着对法院工作和审判实务的了解,以及与信访人的“磨合”,辉哥不再经常“红头胀脸”了,因为他自己总结了一套处理办法,叫“对事对人”。来了信件以后,先查阅所涉案件信息,搞清楚当事人的年龄、学历、工作等背景资料。电话沟通时不着急说,先听,揣摩对方心理,容易沟通的就及时解决问题,案结事了;遇到不容易沟通的,不较劲,先让对方说,等到对方说累了、说不动了、愿意听了,再伺机化解矛盾。因为这样,很多时候一个回复电话要耗费一个小时时间。但辉哥好像不觉得这是一份负担。“就算要打2个钟头电话,最后能听到当事人一句‘谢谢’,也不算白干。”我总能感受到辉哥说这话时的骄傲。
下班后,辉哥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小子的学习上。小子上初三,我觉得他的压力比孩子自己都大。孩子写作业时,他就拿本书在边上陪写到半夜。为了补功课,他给小子报了辅导班,自己就一天天地在旁边陪听。辉哥知道这可能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,也了解有些家长的教育方法更加“轻松”,陪着孩子一起玩,等孩子玩累了、玩腻了,自然就不用多管了。但辉哥说,他可不敢赌。
除了小子的学习,沧州老家是辉哥的另一份牵挂。去年5月份,老家盖房子,辉哥请了年假回家帮忙,回来时整个人像刚参加完新兵训练,一身“健康”肤色。8月份,老父亲生病,在老家做手术,辉哥在跟前服侍,老人术后休养期间每周末回家照顾,周五下班后坐火车走,周日晚上坐火车回来,来来回回奔波近一个月。之后身体没绷住,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,在药堆里泡了十多天。老家的地发生纠纷,辉哥也要利用周末时间坐火车回去解决。他说,对于老家人来说,“地”的事不是小事,那是根。
这就是一名部队“老兵”、法院“新兵”辉哥的故事。尽管这些故事太过平常且零零碎碎,但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到现场来“听”。这会辉哥正敲键盘呢,用速度不快、但挺熟练的五笔输入法,一个个地登记录入信访案件。之后,他要整理复印信件、填好呈批表送领导审批。之后,他要用cocall给内勤们发信息,等着他们来上门取信或者把信送到庭里去。之后,他要给市院监察室的王姐打电话,请教信访系统信息录入问题。之后,他要给信访人打电话,回复已经处理的信件情况。之后,他要给孩子老师发微信,问问昨天为什么儿子八点多才到家。之后,他要和军转办联系,问问什么时候能办转户口的手续。之后,他要……。总之,辉哥总处于忙忙碌碌之中,因为他觉得,虽然在部队算个“老兵”,但到法院之后自己是个“新兵”,要学的很多、要问的很多、要看的很多,要做得更多!